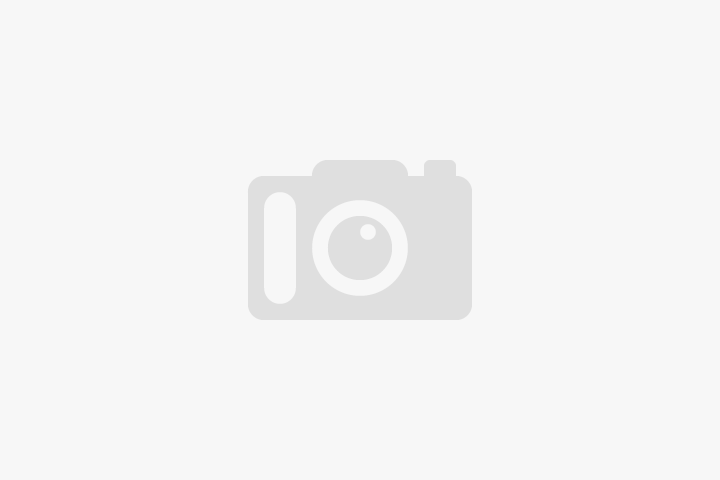微信扫一扫

巴西“神奇教授”的中国缘

中国承建巴西科考站,南极成中巴合作亮点。新华社
【南美侨报网讯】在南极科考超过1000天,著书27本,在自家建博物馆从事科普教育,开私人飞机飞错航线被误为毒贩……巴西生物学家雅伊尔·普茨克的工作和生活有些不可思议,而这名“神奇教授”还有不少与中国有关的故事。
与中国的烟草缘
新华社报道,作为生物学家,普茨克教授与中国烟民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南里奥格兰德州是巴西烟草种植的大州,大量烟草出口到中国。为了保证出口的烟草质量过关,没有病虫害,位于南圣克鲁斯大学的生物实验室起到关键作用,而这个实验室的负责人就是普茨克。
普茨克的研究领域是真菌。巴西烟草有些存在霜霉菌,这是一种对烟草来说具有毁灭性的病菌,如果带有霜霉菌的巴西烟草进入中国,后果将不堪设想。从1992年起,普茨克领导的实验室就对每一批出口中国的烟草进行检测。普茨克还进行检测霜霉菌的培训,20多年来共培训3000多名技术工人,可以在烟草收获和生产过程中进行第一道检测。
今年初,普茨克受聘于附近的潘帕联邦大学,实验室交给助手阿德里亚娜负责。但是他说,“我和中国的烟草缘永远不会终止,只要中国朋友有需求,我肯定会第一时间赶回来帮忙。”
与中国的文化缘
在普茨克家的院子里,可以看到一个练习咏春拳的木人桩。普茨克从18岁开始学习功夫,与所有上世纪80年代时的巴西青年一样,他也被当时风行全球的功夫片迷住了。他专门学习咏春,这份热情感染了儿子,现在父子俩一起练习,共同切磋。
认识许多中国朋友后,普茨克开始收集中国特色工艺品,中国结、中国折扇、中国酒瓶都成为家中的装饰。而他最喜欢的是一架中国战斗机模型,因为普茨克是飞行爱好者,除了真菌类和南极科考的书籍外,他还专门写过一本关于巴西飞行先驱桑托斯·杜蒙特的书。
2015年他首次到访中国,去了北京、上海和云南;2016年他又到北京参加培训,并游览了苏州、杭州和上海。亲眼见到的中国,与他此前从媒体中得来的印象差别不少。“当我登上长城,站在烽火台上眺望时,看到的是漫山遍野的绿树,看到中国在积极地人工造林,为改善环境做了很多工作。而这些工作在西方媒体上我从来没有见过报道。”
普茨克家中有一个博物馆,收集了各种植物标本、古生物化石、飞机模型和介绍南极知识的模型。他说,建私人博物馆的目的就是让前来参观的孩子们从小接受环保的概念。关注环保的他一边介绍博物馆,一边对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绿色发展”的内容赞不绝口:“我看到中国把环保作为国家的发展战略提出,这非常了不起,中国为全世界做出了表率。”
与中国的南极缘
普茨克第一次南极之行是在1986年,他当时17岁,刚刚上大学。现在他前往南极的次数逾20次,累计超过1000天。
巴西在南极地区的科考始于1984年,但是费拉兹科考站规模不大,2012年在一次大火中被彻底摧毁。即使是没有失火前,巴西很多科考人员在南极都只能自己扎营住帐篷。
在南极那片遥远的大陆上,世界各国的科考人员互相帮助是常态,结识中国科考人员的故事也不例外。普茨克说:“有一天我们正瑟缩在帐篷里,听着外面呼啸的寒风,忽然电台里中国长城站的同行发出呼叫,问我们愿不愿意到长城站过上几天。”
“那还用问吗?我们立刻答应了。长城站的人员派直升机来接我们,然后我们就进入了长城站温暖的营地,有暖气,有热乎乎的饭菜。他们给我喝了一碗汤,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汤,但绝对是我这辈子喝到的最美味的汤!”普茨克现在说起来似乎还在回味。
跟普茨克一起被邀请的还有俄罗斯、乌拉圭、智利等国的科考人员,原来长城站是在庆祝中国的新年。“中国的同行们非常热情,大家围在一起包饺子,然后彻夜庆祝,让我在世界最寒冷的地方感受到满满的温暖。”普茨克一边说着,一边让夫人找出中方工作人员送给他的南极站纪念币。
自那以后,几乎每次去南极,普茨克都要到长城站转一转。1992年,普茨克还与中国科考人员共同发表过关于南极真菌的专业论文。
如今,中国正在帮助巴西重建南极科考站。今年年初,普茨克看到科考站已经初具规模,一座现代化的崭新科考站将很快可以投入使用。普茨克说,他目前正与中国科考人员一起推动金砖机制框架下的南极科学考察合作,相信今后两国间的关系会更加紧密。
■链接:中国承建巴西科考站 南极成中巴合作亮点
新华社报道,2017年9月,随着中国企业预制施工阶段结束并完成预拼装验收,巴西费拉兹司令南极科考站(简称费拉兹站)重建所需设备和材料将从上海港装船,运往南极乔治王岛组装。作为中国企业承建的首个外国南极科考站,因大火焚毁的费拉兹站即将“重生”,成为中巴这两个金砖国家的合作亮点。
中巴合作“水到渠成”
新华社报道,乔治王岛是南极洲的“地球村”。地理位置相对易达,又是延伸至南极大陆科考的跳板,这里集聚了40多个各国科考站,占南极科考站总数的一半还多。离费拉兹站建站地30海里之外,便是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
谈及中国与巴西合作建设科考站,中国南极长城站、中山站与昆仑站总设计师、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极地建筑研究中心主任张翼用“水到渠成”来形容。
“毫不谦虚地说,长城站是乔治王岛上最好的科考站,在那边的影响力非常大!”张翼说,长城站在设计阶段就充分考虑了施工便捷性,中国极地考察“十五”能力建设期间长城站扩建速度惊人。当时附近的韩国站也在更新,其他科考站询问:“为什么你们的施工人员只有韩国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而建设速度却要快得多?”
张翼说,2008年,中国在南极冰盖最高点、海拔超过4000米的冰穹A地区建设中国首个南极内陆考察站——昆仑站。当时,昆仑站与德国诺伊迈尔Ⅲ科考站不约而同首次采用一种新的“全装配式”建站模式,即内部是预制的集装箱功能模块,外层是现场安装的保温板,全部模块运至南极组装。
南极环境恶劣、运输遥远、现场支撑条件薄弱、人力短缺且可建设周期极短,在种种不利情况下,昆仑站建站模式既能把现场施工量压到最少,又能保证建筑极高的保温与密闭要求,是近年南极建站的主流方式。
中国在南极成功的实践经验坚定了其他国家寻求合作的信心,南美多国相继抛来“橄榄枝”,寻求中方帮助建站。2015年5月,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击败多个国际竞标方,成功中标费拉兹站重建工程。
费拉兹站重建项目的设计方是来自巴西和葡萄牙的设计公司,采用的正是中国10年前开始应用的全装配式建造模式。该站总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米,由226个集装箱式的模块组成,分东区、西区和技术区,配有实验室、设备用房、图书馆和生活娱乐等各类设施。
中国企业“钟表级”施工
费拉兹站所在区域位于南纬62度,接近西风带,一年中平均6级以上的大风天达百分之六七十,中方项目组今年11月登岛时积雪预计在两三米左右……“在国内盖一个10万平方米的大楼,难度不及在南极建一个几千平方米的科考站。”曾17次去往南极,其中7次作为中国南极考察队领队的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原党委书记魏文良感慨道。
“巴西建站说白了是一个‘交钥匙工程’,人家一张图纸交给我们,我们要把它变成宏图落地于南极,无论是材料、设备、物流、现场组织,整个链条都由中国来承担。”
原费拉兹站建于1984年。2012年,一次发电机组故障引发的火灾使其付之一炬。重建中,安全问题始终是负责南极科考的巴西军方首要关切,随之而来的是各类严苛的标准要求,巴西军方、费拉兹站设计方和中国施工企业跨越文化和语言障碍,无数次地沟通、建议和修改。
费拉兹站联合设计方、负责结构和设备专业设计的葡萄牙公司AFAconsult首席执行官鲁伊·富尔塔多说,该站的设计如同精密的瑞士钟表制造,所有部件和系统必须要以高度精确的水平建造,才能和谐运作、发挥功能。
南极只有4个月的施工窗口,所有时间都要用来组装,所有一切都要提前准备和考虑。预制阶段哪怕几毫米误差的小瑕疵,也可能造成组装中的大麻烦。为实现现场100%的顺利装配,中国企业必须拿出“钟表级”的建造和施工。
在扬州的集装箱装配现场,中国通利冷藏集装箱有限公司的项目工程师黄必和说:“最复杂的组合箱是一个三合一的筛检室,45平方米左右,内有水族箱供采集样本、分类使用等,里面管线多得数不过来。”
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费拉兹站建设项目组经理曹虹说,鉴于设计的高精度,费拉兹站建设已经不是钢结构要求水平,而是机械加工精度要求,整个项目采用了先进的全装配式施工工艺和建筑信息模型技术。
打造南极合作“新样板”
魏文良表示,中国开展了30多年南极科学考察,无论是科学考察、站务管理、基础保障、建设和物流,在当今世界南极科考大军中都“是强者也是佼佼者”。今天南极考察任务越来越多,区域越来越广,如何利用商业性操作把资源用于科考,通过商业模式建站和维护,中方建设费拉兹站过程中,对未来支撑极地科考的新模式进行了有效探索。
“很显然对巴西人来说中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太令人吃惊了,施工速度、质量、工厂的规模,这在巴西很难见到!”已派驻中国一年的巴方顾问马尔塔对中国企业的施工能力点了一个大大的赞,“在南极建站要求异常严苛,中国施工企业和中电团队做到了严肃对待。”
巴西海军少校、项目监理负责人何塞·科斯塔·多斯桑托斯评价说,在这次积极的合作中,两国共同利用各自的极地经验解决了问题,促进了项目的改善,未来寻求南极科学与技术研发合作的可能性始终存在。
“两国的南极科考项目有着共同目标,合作可以更为积极,我们可以加强不同领域的科研交流和彼此的物流支持。”他说。
独行快,众行远,在冰天雪地的南极更是如此。无论是推动商业化共建科考站,还是联合极地科考,金砖国家多边和双边层面合作在南极还有诸多潜力可挖。
(编辑:晓舟)
-

Downtown Genebra待售
圣保罗SP 0元/㎡ 价格待定 -

Sweet Vila Nova待售
圣保罗SP 0元/㎡ 价格待定 -

Estação Brás待售
圣保罗SP 0元/㎡ 价格待定 -

Downtown República待售
圣保罗SP 0元/㎡ 价格待定 -

Face Home Life待售
圣保罗SP 0元/㎡ 价格待定 -

Apartamento 3 dormitórios 62m vila guilherme zona norte待售
圣保罗SP 0元/㎡ 价格待定 -

My Place Paraíso待售
圣保罗SP 0元/㎡ 价格待定 -

MaxHaus BLX待售
圣保罗SP 0元/㎡ 价格待定 -

鼎尚华庭售罄
联邦州BRA 0元/㎡ 价格待定 -

水榭春天待售
0元/㎡ 价格待定 -

灿邦广场待售
0元/㎡ 价格待定 -

御岭公馆待售
0元/㎡ 价格待定
-
 圣保罗SP53㎡| 2室1厅 1200元 面议
圣保罗SP53㎡| 2室1厅 1200元 面议 -
 圣保罗SP100㎡| 2室1厅 0元 面议
圣保罗SP100㎡| 2室1厅 0元 面议 -
 圣保罗SP61㎡| 1室1厅 600元 面议
圣保罗SP61㎡| 1室1厅 600元 面议 -
 圣保罗SP80㎡| 2室1厅 900元 面议
圣保罗SP80㎡| 2室1厅 900元 面议 -
 圣保罗SP93㎡| 3室2厅 1400元 面议
圣保罗SP93㎡| 3室2厅 1400元 面议 -
 圣保罗SP42㎡| 1室1厅 1512元 面议
圣保罗SP42㎡| 1室1厅 1512元 面议 -
 圣保罗SP103㎡| 3室2厅 4710元 面议
圣保罗SP103㎡| 3室2厅 4710元 面议 -
 圣保罗SP142㎡| 3室2厅 6200元 面议
圣保罗SP142㎡| 3室2厅 6200元 面议 -
 里约RIO156㎡| 3室3厅 3100元 面议
里约RIO156㎡| 3室3厅 3100元 面议 -
 里约RIO56㎡| 2室1厅 1200元 面议
里约RIO56㎡| 2室1厅 1200元 面议 -
 里约RIO140㎡| 3室1厅 2700元 面议
里约RIO140㎡| 3室1厅 2700元 面议 -
 里约RIO280㎡| 4室2厅 6800元 面议
里约RIO280㎡| 4室2厅 6800元 面议
-
下一条:物美价廉 巴西人也青睐义乌小商品
0条评论
推荐
投稿
我要投稿新帖
我要发帖-
敏感货专线#专题讨论#
2025/10/30 16:43:07 巴西货代
巴西货代 -
从中国海运家具到新西兰奥克兰,惠灵顿,基督城省心省钱全攻略!#新人报道#
2025/10/30 14:40:43国际物流kevin -
从淘宝网购家具海运到澳洲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省钱省心攻略!#弱弱提问#
2025/10/29 11:30:57国际物流kevin -
从中国淘宝网购家具海运到新加坡:终极省钱省心全攻略!#专题讨论#
2025/10/28 17:47:53国际物流kevin -
新加坡生活版:家具,沙发,餐桌,椅子海运到新加坡运输操作指南#弱弱提问#
2025/10/27 17:54:28国际物流kevin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